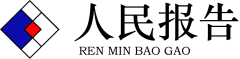全国政协“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口易地搬迁”专题调研报道 稳
抬头,眼前是丛林覆盖的连绵群山;
低头,脚下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路。
如果不是记者亲眼所见,很难想象在这四面环山的山坳里,还生活着这样的人家:房子是用简陋的木板搭建起来的二层小楼,一楼是羊圈、狗舍以及堆放杂物的地方。几块破旧的塑料板、木板把二楼隔成了几间卧室、厨房。目光所及之处,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墙角的一台老式黑白电视机是唯一的家用电器。
“一到过年,家里会挤着十几口人。有父母、五个兄弟姐妹,还有亲戚、邻居。”在家排行老二的春芳告诉记者,“我们不敢搬出去:没有收入,也不适应外面的环境,没办法生活。”腼腆的春芳看上去大概20岁出头,她一边和记者聊天,一边哄着怀中刚满一岁的妹妹。
这是记者跟随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专题调研组在广西都安县大兴镇国龙村吞屯队看到的一幕。虽然吞屯队曾有3户已经搬迁到拉温扶贫生态移民点,但依然还有11户51人留守在这里。年轻的男子以外出务工为主,老人和妇女则在家中照顾小孩,平时以种植玉米、桑叶、牧草维持生计,人均耕地0.55亩。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吞屯队群众生活水平相对较低,2015年人均纯收入仅有3150元。
“我不识字,再加上这里没修路不好走,出去打工也不方便。我大姐在广东打工,有时会寄回来一两千块钱,一般都给弟弟妹妹上学用了。”春芳说,她有两个读初中的弟弟和一个读小学的妹妹,每天凌晨四五点钟起床,翻过眼前这座山,再走到城里去坐车到学校。记者算了算时间,从在路边下车徒步走到山坳里,大约用了40分钟。“冬天早晨太黑,就拿个手电筒;要是遇到雨天山路很滑,就很危险。”春芳补充道。
在和村民交谈中,调研组听到不少这样的声音:“要我们搬也行,但以后怎么生活?”“在这里还能靠土地生活,出去了啥也没了,没有收入,只有一个空房子。”“山外面那个环境不习惯,不适应。”……
这样的声音,让调研组成员,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湘西州政协副主席田岚颇有感慨:“土地是农民的根,让他们离开自己祖祖辈辈守护的土地,这的确需要勇气。‘要我搬’和‘我要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需要农民的传统思想有一些转变。如果群众不是自愿搬走,那他们还会再折返回来。除非有就业保障,给他们提供收入来源。”
对此,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表示赞同。他认为,易地搬迁要充分了解群众需求,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为搬迁对象提供多渠道的就业方式,保证群众的基本生活,完善搬迁后续扶持政策,从而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
这些观点在位于都安县城3公里的“八仙农民城”得到了印证——宽敞整齐的街道,热闹的商店,让人完全想不到这里曾是乱石横陈、杂草丛生的贫困村。作为扶贫移民区的示范点,“八仙农民城”始建于1994年10月,有大石山区贫困农民1100户5100人迁入安置。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基础建设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齐全的宜居小城。在社区街道两旁,记者看到每家每户都有三三两两的妇女们在忙碌着。原来,她们正在做竹藤草芒编织加工的订单。“编一个竹篓大概1小时,3块钱手工费,多劳多得。在家也是闲着,编一些可以挣点零花钱。”一位大姐乐呵呵地对记者说道,细长的竹藤在她的手指间熟练地缠绕,一个竹筐雏形渐渐显现。据了解,八仙城的编织业是在社区能人、今年62岁的蓝炳芬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蓝炳芬一家七口,2004年从贫困村甘湾村移民到八仙城,利用当地的资源从事竹藤草芒编织加工,当年家庭收入就达到7000元。在他的带动下,所在街道近20户居民也加入到编织加工行业,编织的产品远销到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而“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成功推广,有效地解决了搬迁户就业和增收问题。
与社区能人带动创业不同,大化瑶族自治县的生态民族新城则是通过“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产城结合”的方式,为搬迁对象提供更多、更适合的工作岗位。新城规划总用地面积3158亩,规划安置1.5万户约6万人,被列为“易地扶贫搬迁与城镇化结合试点工程”。区内设置商业、移民创业园、物流园、民族工艺品交易市场等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为搬迁户提供广阔的后续发展空间。创业园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入驻的企业和搬迁户可享受一系列的扶持政策,例如免租金或低租金铺面、给予就业困难群体1500元到2000元的一次性补助、帮助自主创业者或者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申请小额担保贷款贴息,开设免费的农民创业就业培训等等。
朱维群表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处理“要我搬”和“我要搬”的关系上,关键还是要因地制宜制定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充分发挥搬迁对象的能动性和积极性,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提供就业岗位、有组织的引导农户外出务工等方式,保证他们的收入来源,化被动脱贫为主动致富,防止脱贫再返贫。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人民报告立场。